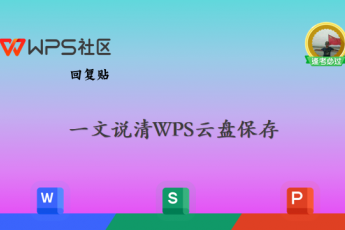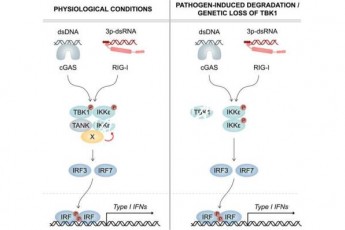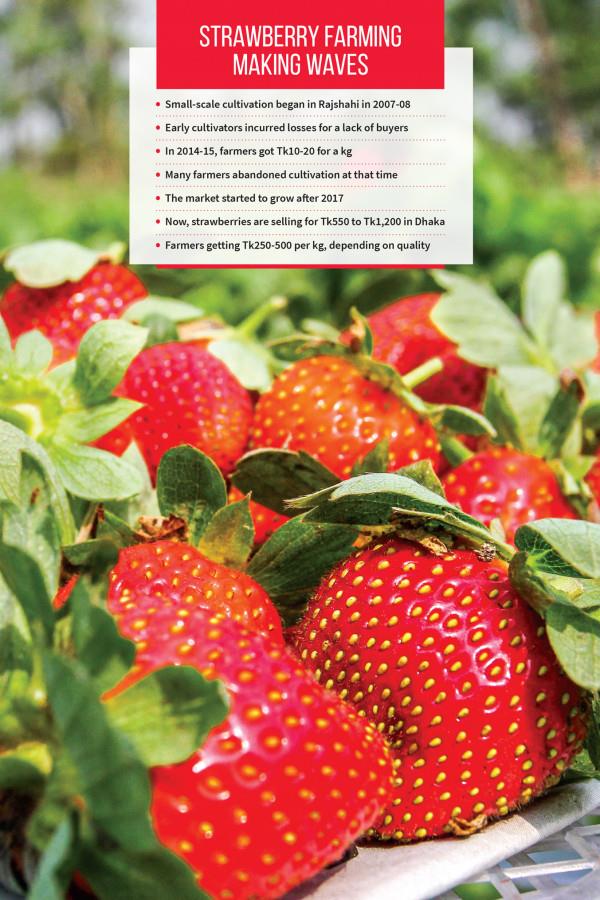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耶路撒冷做精神科医生,负责管理上锁的病房,为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服务,他们因为需要24小时的护理而无法留在社区。
这种生活,实际上是以色列的大部分生活,现在感觉很不稳定。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空袭警报已经开始在耶路撒冷响起。将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与大屠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自满情绪已被粉碎到何种程度。
加沙居民的处境要糟糕得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6岁的儿子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他躺着,一颗炸弹落在他身上,我很不安。我不愿与那些带着血淋淋的孩子进入加沙急诊室的家庭交换位置,在伤者和死者之间,除了地板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休息。只是写这些字,我就哭了。我感到愤怒的是,哈马斯明知自己犯下的暴行,却心甘情愿地招致这种报复。
外国读者如果认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生活充满了持续不断的相互仇恨和复仇的欲望,那就情有可原了。这种敌对情绪大量存在,但更多的是在实地发生。而积极变化的发生地往往是工作场所。
我工作的以色列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可能是这个国家最一体化的部门。大约一半的医疗执照获得者是阿拉伯人(包括德鲁兹人),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即将毕业的护士、药剂师、甚至牙医都更可能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医院的病人可以得到多民族专业人员的治疗。在这样的时刻,当许多犹太人被征召去做预备役时,通常不服兵役的阿拉伯人的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几代人以前,医学是一代犹太人进入受人尊敬的美国社会的门票,最终也为他们打开了其他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在科技等其他专业领域的代表性仍然不足,但对他们来说,医疗保健是雄心勃勃、有能力的学生的热门职业选择。长期以来,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教育体系在资金和结果方面都是分离和不平等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已经进行了投资。这样做不仅将使我们更接近于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而且也将使我们更接近于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
我的工作日(偶尔还有晚上)都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度过的。我从1986年开始从事精神病学工作,当时我离开纽约,在耶路撒冷安家。两年前,我受命负责管理耶路撒冷最活跃的住院病房——卡法·绍尔医院(Kfar Shaul Hospital),该医院坐落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这里曾经是阿拉伯人的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据报道,1948年犹太人(当时还不是以色列人)军队在这里屠杀阿拉伯村民。这个地方充满了历史,但大多数人在日常活动中都设法忽略了这一点。然而我病房的员工是高度融合的。五个精神病医生中有三个是阿拉伯人。护士长和近一半的员工是阿拉伯人。大约四分之一的病人是阿拉伯人,大部分来自东耶路撒冷。这根杖是连贯的。我们是一个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的团队。
属于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两个部落的工人之间的热情是真实的,令人振奋的。我们参加彼此的家庭婚礼,我们中的一些人一起度假。我们允许自己善意地取笑彼此的宗教习俗。就在最近,当一个基督徒病人偷偷带了一些被禁止食用的火腿进入病房时,我们感谢他让犹太人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我的不科学的印象是,在单独工作或只与他们的宗教伙伴一起工作的熟人中,恐惧和怀疑的程度更高。例如,我在犹太教堂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结束了预备役,回家过安息日,他兴奋地向我讲述了目前的情况。(我认为犹太教比其他一神教更能容忍礼拜期间的闲谈,但我不希望在这一点上受到事实核查。)我们正在谈论南部的哈马斯袭击和北部的真主党威胁,他严肃地告诉我,“有一个更大的威胁正在逼近,我们必须克服它。”
“伊朗?”我问。
他轻蔑地摇了摇头。我被难住了。
“贝特·采法法,”他解释说,指的是附近的一个阿拉伯社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耶路撒冷。他在平民生活中不与阿拉伯人合作。如果他知道,我想他不会相信的。
我们的同教者之间发动的战争如此接近——穿越加沙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距离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汽车,或者一分半钟的导弹——威胁着撕裂这个脆弱的社会结构。
我担心的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的医院工作人员没有公开谈论他们的感受。早上的问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形式,常常很快以公式化的祝愿结束,祝愿我们听到好消息。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带着这样的想法,一天下午,我召集了一次员工会议,20个人几乎按种族平均分配,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小心翼翼地开始谈论在一个毁灭的时代来工作。对犹太人来说,参与似乎更容易: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更有信心。许多人说,上班就像回家一样,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提供的服务中团结在一起。阿拉伯人一开始比较犹豫。他们知道,在工作场所之外,他们背负着被怀疑的负担。其中一个人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他在加沙的朋友反对哈马斯,但现在带着年幼的孩子从遭到轰炸的北部逃往南部不确定的安全区。另一个人描述了他对回到他经常锻炼的健身房感到怀疑,以免他被要求离开。担心在街上游荡的潜在义务警员的报复是一个普遍的主题。
会议结束了,但人们仍留了下来继续谈话(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在其他员工会议上,人们迫不及待地分散开,继续工作),分成两三个充满活力的混合小组。我觉得我们跨越了一个障碍。我更多地了解了加沙居民的悲惨绝望,他们是哈马斯的敌人,无处可逃。看不见他们要容易得多。我觉得和所有员工都很亲近,不分种族。
伦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加沙无名的孩子们
工作是这些联系和对话最自然发展的地方。如果我们培养这种已经在许多地方开花结果的接触,同时尽量减少双方强大的民族孤立主义者和至上主义者的影响,或许还有希望实现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未来。
我不想代表我的阿拉伯同事说话。虽然我和他们很亲近,但我知道他们在这种悲惨处境中的看法必然与我不同。我偶尔会发现,有些人有所保留,不确定我能被信任到什么程度。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更仔细地斟酌我的话吗?种族分裂加深了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本质鸿沟;在我们周围爆炸的炸弹在那里留下了弹坑。我知道,要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需要的远不止偶尔的员工会议,这种紧张局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整个部门。
然而,我抓住了我所建立的联系,并在这些遭遇中找到了力量。我不会忘记,在10月7日的野蛮袭击发生后的那个早晨,我被暴行的程度震惊了,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发现一位资深护士,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独自坐在那里,焦虑地抽着烟,看起来比这位精力充沛、有魅力的人平时更孤僻。他在这个部门工作了多年;在所有员工中,只有我的意第绪语说得比他好。
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我们悲伤而恐惧地试图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谈到了狂热的罪恶,他试图向我解释这些暴力行为对《古兰经》的亵渎。
我迟疑地告诉他我的幻想:“我想象自己被这些凶残的混蛋绑架了。就在他们要割我喉咙的时候,我设法说服他们允许我打一个电话。我拨,你接。你通过扩音器向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犯下这种可怕的罪行。”
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自信地说:“打电话给我,我会和他们谈谈,告诉他们!”
灾难发生以来,我第一次隐约感到一丝希望的刺痛。